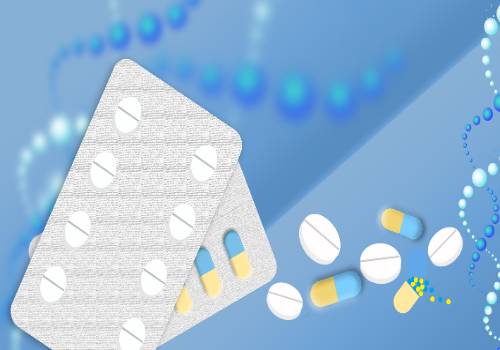当前讯息:青铜器“葆调”考
“葆调”是一件形制奇特的青铜器。观其造型,有一部分状如插头,还带穿孔;有一部分颇似锁具,仿佛还有关节可以活动,极富科技感。汉代作器的主流还是使用范铸工艺,要想在一握之间巧思妙构出这么一件既带弧还有洞甚至有活环的器物,殊非易事,即使是现代的工匠都未必能够模仿还原。
图1 葆调侧影
图2 葆调俯视图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图3 葆调铭文
该器曾经罗振玉收藏,并收录在其编刊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中。另外,《汉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也做过收录。但对其用途尚未有定论。罗振玉是甲骨四堂之一,学术地位极高,近两年的专题展览逐渐丰富起来。非常幸运,“葆调”也随着罗振玉其他旧藏开始巡展,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至少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学术高峰——罗振玉藏品展”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成就展”两场展览中露过相。这件“葆调”目前藏于旅顺博物馆,根据展签可知该器基本信息:“长9.82厘米,宽1.75厘米,高5.4厘米,呈扁长方体,中空,两件器物组成,有多处方形、圆形孔。一端有铭文8字。”
葆调何用
近距离观摩此物,直面古人高超铸造技术的冲击,首先会犹豫一下器物年代。器物铭文具有典型汉代风格,后世颇难伪造,当可打消疑虑。料想每位见过此器的观众,都会油然而生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件器物究竟是作何而用。好在铭文已有提示,不然我们连它如何称呼都要成谜。铭文共八字,后六字清晰可辨——“毕(畢)少郎作葆调(調)”。前两字连接过密,倒是不好判断。
关于葆调铭文的释读,罗振玉的观点独树一帜,《贞松堂集古遗文》有载:“潍县陈氏旧藏,今归贞松堂,器名葆调,不知何用,(上日下羊)即皋字”。可见罗振玉认为葆调铭文的第二字为“皋”。另外,2019西泠春拍“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出现一件罗振玉题跋金石拓本团扇,题识:“汉葆调。王皋毕少郎作葆调。葆调状如钥,不知何用,潍县陈氏簠斋旧藏,今归雪堂。辛酉(1921)六月雪翁手拓并记”。钤印有四:二万石斋(白)、雪堂手拓(白)、上虞罗氏(白)、叔言只古(朱)。若根据罗振玉的观点,葆调铭文则为“王皋毕少郎作葆调”。
图4 罗振玉题跋金石拓本团扇
毕少郎是人名,王皋看似也是人名。不过,一者为姓名俱在,一者只见姓氏,不合逻辑。容庚在《金文续编》中有注:“贞释青羊为王皋”,直言前二字应为“青羊”。首先,“上日下羊”释“皋”不通。而且,“青”字下部并不是“日”,而是“月”。“月”为“丹”的变体,《说文·青部》:“青,……从生丹”,因此“王皋”应为“青羊”。这是在汉镜铭文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也可与此相互印证。
为了弄清“葆调”究竟有何用途,笔者决定分而划之做一拆解,分别琢磨两字含义。同时代的汉简文献中便有“葆”字。相关学者著文专门探讨“葆”字的各种释义,大约是随“保”字,具体有担保、保养、保卫、守卫等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特征。(马智全:《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葆”探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显然是与器物不搭边的。以上都是文字的引申义,原意可见《说文》。“葆”为“草盛貌”。但是“调”字作何解释?《说文》:“调,和也。从言,周声”。检索二字,可寻一些尺牍中出现“精加葆调”、“益辅葆调”、“益冀葆调”、“良务葆调”等记载。此处所言之“葆调”是“葆养调和”的含义,显然和铜器无关。
关于葆调的记录,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早在罗振玉之前,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存在一段记述:“又月之初九日,韩兄至苏,奉到手制三通。一为二月十七日书,一十八日书,一廿三日书,附来古匋拓本三总,包计二千三百卅三种,又瓦量十字拓正副二气,又古鉥拓二古印,一葆调拓,一浣手。展诵但觉古色古香,迸溢几案,以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吴云:《两罍轩尺牍》卷九,第80页)这位“韩兄”是吴大澂的外祖父韩崇。吴云在信中仅表示见过葆调的拓片,并评价其为“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可惜未对该器展开更多解释。
图5 秦始皇陵1号铜车伞柄
目前能见到对“葆调”有过解读与分析的只有马衡。他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专辟“葆调”词条:“葆调者,编羽葆之器也,旧藏潍县陈氏。形如今之铜锁,一端有隶书八字,曰‘主(上日下羊)毕少郎作葆调’,盖汉物也。按汉书韩延寿传,‘植羽葆’,颜师古注曰‘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轟之类也’。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曰‘葆车,谓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为葆’,是此器乃施于车盖,其孔所以饰羽。名曰葆调,其义未详。或以其合聚五采,有调和之义欤?”(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上),《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一,第55页)马衡对铭文的释读与罗振玉和容庚的都不相同,认为前二字为“主(上日下羊)”,但他也未作考证。不过马衡对“葆调”的考证相当仔细,他主要依据“葆”字含义联想到“葆车”上的“羽葆”,并认为“葆调”是用于固定马车盖上羽饰的器件,这样大约可以说通。不过想来还是觉得蹊跷,如果仅仅为了装插羽饰,就设计出如此繁杂的造型和机关,实在有些小题大做。或许马衡所下具体结论存在偏差,但关注的方向无疑非常正确,“葆调”是和葆车紧密相关的器物。或许,相同类型的器物已有考古发现,只是因为不具铭文而湮没其名。
图6 秦始皇陵1号铜车伞杠与伞座连接关系示意图示(图片引自郑岩:《机械之变——论秦始皇陵铜车马》,《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
笔者决定在考古发现的青铜车马中寻求线索。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1978年秦陵封土西侧出土的两乘秦铜车马。这两乘铜车均驾四马,即两骖两服,主体部分均以青铜铸造,少数构件采用金银,通体外施彩绘。其中1号车为立车,车马通长225厘米,通高152厘米,总重1061公斤。(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看似平常的马车,车舆中央树立的高杠车伞则暗藏玄机。伞座呈十字形,包括了活铰、曲柄销式闭锁等结构,通过推拉组合,可以灵活控制伞柄在底座凹槽滑动,从而便于调整伞盖合适的倾斜方位。凹槽暗藏榫卯,既可锁定伞杠,又方便分离。若遇刺客袭击,不固定的连接使得铜伞随时可以取出,伞盖作盾,伞柄和内藏利刃都能用于自卫反击。为了稳固伞柄,伞柄还有扣锁杆,杆上有一活扣,类似的圆环型活动插销,可以锁住伞柄中部,以防剧烈运动时伞柄折断。仔细辨识,伞柄顶部装纳活动直销的方机关也为长方形,几乎和“葆调”造型一样。其具体的操作原理如同现在的碰锁,纪录片《镇馆之宝》第七集《秦始皇陵铜车马》对此构件有着最为直观的讲解与诠释。秦陵1号车并无车盖,广义而言,伞盖也可视为葆盖,若论该青铜构件的功能为“调节葆盖”当是恰如其分。
据统计,1号铜车马上发现31处文字,共计58字。其中5处朱书文字,共9字;26处刻文,共49字,字体均为带有较浓篆书意味的隶书。由于刻文笔画纤细,青铜锈蚀,字文大多漫漶不清。可惜未在伞柄伞盖等位置发现文字。虽无法明证伞柄顶部的长方构件就是葆调,但是根据其独特的造型和同样的功能,两相比照,足可肯定此器即为葆调。
少郎何人
葆调八字铭文中的“毕少郎”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少郎”的称谓还见于1989年江苏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永平四年(公元61年)画像石,上刻共35字隶书题记:“建武十八年腊月子日死,永平四年正月,石室直五千,泉工莒少郎所为,后子孙皆忌子。”(王黎琳、李银德:《徐州发现东汉画像石》,《文物》1996年第4期)其中的“莒少郎”,是营造墓室的工匠名字,符合物勒工名的制度。同理,毕少郎正是制作葆调的匠人。
《说文》释“郎”为“鲁亭也。从邑良声。”郎即古“廊”字。原指宫殿廷廊,置侍卫人员所。因为侍从官总是站在走廊下,以便随时听候皇帝的命令,便有此谓。《后汉书·桓帝纪》注:“郎官,谓三中郎将下之属官也。”可见郎在两汉时期是官名,为帝王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称。郎官一直沿用到清朝,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差遣等侍从之职。
图7 铜山永平四年画像石题记
与“少郎”相近的“少为郎”是汉代宫廷多见的情形,大约与“少年吏”相当。比如,《史记》卷三三《韩王信传》载:“(韩)增少为郎”,卷六〇《杜缓传》载:“(杜)缓少为郎”。《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写道:“(袁)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郎”以特殊方式参与行政操作,因为与帝王关系的亲近,可以施行有力的影响。有的甚至“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王子今、吕宗力:《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南都学坛》2011年第4期)
由于郎官们一般都由青壮年男子担任,所以“郎”字引申为对一般年青男子的尊称。《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写道:“策时年少,虽有位号,而士民皆呼为‘孙郎’”。周瑜被称为“周郎”,更是人尽皆知的故事。更为极端的例子见于《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沈)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车语乎?’”尊称十来岁的少年甚至是儿童为“郎”,这也许便是后来民间盛行“儿郎”、“少年郎”称谓的滥觞。(同上)
经过几番变化,人们开始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也称为“郎”。比如,流动贩卖日用品的人就是“货郎”;放牛的人便是“牛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肃苑》一折中写有唱词:“预唤花郎,扫清花径”,此处“花郎”便是指管理园中花卉草木的人。
葆调中的“少郎”并无暗指职业的含义,而且也无法与贴近宫廷的郎官相提并论。无论是营造墓室的“莒少郎”,还是制作葆调的“毕少郎”,都属于从事工程的技术人员,地位不会太高。根据“郎”字义的转向,将“少郎”理解为对青年男子的敬称,应无不妥。
青羊何谓
至此,“葆调”的用途以及何人所为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然而,铭文中起首两字仍存疑团。无论是罗振玉判断的“王杲”还是马衡认为的“主(上日下羊)”,在汉代青铜铭文中都遍寻不到,唯有“青羊”是能找见出处的。
在汉末、三国和西晋时期的铜镜上,常常出现“青羊作镜”的铭文。例如,1996年绵阳市游仙区白蝉乡朱家梁子1号崖墓出土的铜镜。钮座外饰一圈神兽纹,左龙右虎,张口露齿,好似相互对峙,二兽尾部隶书“青羊”二字铭文。外区一圈短直线纹,缘上两周纹饰,内为锯齿纹,外为双线波折纹。虽然此镜于四川出土,但是跟青羊宫毫无关系。成都市区的“青羊”之名,是因为有青帝部下的仙童化身为青羊,在此地显灵。晚唐翰林乐朋龟在《西川青羊宫碑铭》写道:“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于蜀国”,便是记述了这一传说。
图8 绵阳朱家梁子出土“青羊”铭文铜镜
罗振玉也对“青羊”有所关注,不过他在《镜话》中承认,“青羊作镜”语殊不可晓。而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认为“青羊”似为人名或商号名,但不知其为何处之人或商号。铜镜铭文不止有“青羊”,还有“三羊”和“黄羊”。王仲殊考证“青羊”为吴郡吴县的镜工之名,同时推断“三羊”和“黄羊”也是作镜工匠家族的名号。(王仲殊:《“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考古》1986年第7期)而刘航宁则持不同意见,以洛阳出土东汉“青羊”铭龙虎镜为例,打破“青羊”镜为吴镜的观点,指出“青羊”铭文镜制作中心实为洛阳。他进一步认为“三羊”指铜、锡、铅三种祥瑞金属,“青羊”为青铜之义,而对于“黄羊”的解释较为模糊,应也是关于铜镜的吉祥语。(刘航宁:《三羊、青羊、黄羊镜铭新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持相似观点的还有汉学家高本汉,他认为“羊”通“祥”,意为吉祥,而“三羊”与“三商”(三种经衡量的金属)、“三刚”(三种坚硬的金属)相似,是指三种吉祥的金属,从而推定“青羊”是指青色的吉祥金属,可与“青铜”一词相比拟。
李振华又有不同见解,他在文中介绍了四川洪雅县文管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铭文神兽镜,镜背有“汉家长宁,黄羊作镜,公卿服者,富贵番昌”,认为“黄羊作镜”中的“黄羊”即战国时期晋大夫祁黄羊,以秉公办事著称。(李振华:《“汉家长宁”铜镜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此说应是受到《金文总集附目录索引》论述的启发。《金索》引娄机《汉隶字源》中记载的一面青羊镜:“青羊作镜亖夷服,多贺国家民息,胡〔反书〕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得天力”亦与此略同。胎字亦误,娄氏又云青羊。阳如欧羊之类。鹏见古溪刻有“青羊君”,殆其人?可见《金索》认为“青羊”或与古溪刻的“青羊君”有关系。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青羊”也可写作“青祥”,是一种吉语,指代优质金属。又解释道镜匠们之后成立了雅号为“青盖”的组织,后来“青盖”渐渐独立,分别代称为“青羊”“黄羊”“黄盖”的作坊。(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第46-110页)
其实,如果结合“葆调”的铭文比对以上几种说法,很容易排除“青羊”为铸镜原料的说法。假设此解成立,葆调上的铭文应为“毕少郎以青羊作葆调”。而“青羊”出现在毕少郎之前作为定语,宾语如何倒置也是不通的。还比如,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枚盘龙镜,内区的主纹为一龙一虎相对峙,靠近龙的尾部有“青羊志兮”的四字铭记。“青羊志兮”中的“志”意为用文字或符号作标记,说明是“青羊”记作的。这也说明“青羊”不应是原料,也不应是地名,而是一个能铸造铜镜的主体。
既然毕少郎是工匠无疑,“青羊”自然为其归属的某一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青羊”应当是一个铸镜工坊的诨名。无论出现在铜镜上,还是在葆调上,“青羊”也应当被视为物勒工名制度的范例。用物勒工名制度来确保产品的质量,渗透在汉代官营机构的各个生产管理领域。汉代的“物勒工名”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工官(生产机构)+监造官员+主造官员+生产工匠;二是工官+官吏名或工官+工匠名;三是仅刻制造机构,工官或亭、市和市府;四是仅刻工匠名。(雷晓伟:《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考古学研究》,郑州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目前出土所见有勒名的汉代器物种类与数量都比较丰富,铜器、漆器、铁器、骨签等器物上均可得见。由此可见,套用物勒工名制度的几种类型,将“青羊”理解为工官,毕少郎是工匠,葆调则是器物名称,非常合理。
汉代的庄园经济已有规模,刺激商品区分等级,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青羊”就是铜镜的一大品牌,而之后诞生的“黄羊”“三羊”“青盖”或许就是模仿成分居多的山寨。也许,作为大宗的铜镜有着严苛的勒铭制度,优秀铸师毕少郎同样心有不甘,便在“葆调”上留下自己的称号,名垂千秋,碰巧成为破解“葆调”之谜的重大线索。
- 当前讯息:青铜器“葆调”考 2023-05-08 17:00:34
- 高会公式记不住?考试带上这个如有神助! 2023-05-08 16:58:31
- 第二十九天-初级会计实务考前30天突击学习:利润表的编制 2023-05-08 17:16:40
- 环球观点:中考作文素材:宝藏词汇推荐四 2023-05-08 17:04:41
- 哪里招bim工程师哪里招bim工程师最多 环球视讯 2023-05-08 17:07:34
- 环球精选!中考作文素材:宝藏词汇推荐三 2023-05-08 17:01:44
- 消毒规范保健康 成都三十七中召开食堂及物业人员培训会 2023-05-08 17:08:21
- 中考作文素材:满分句式推荐二 2023-05-08 17:17:41
- 全球速递!中考作文素材:满分句式推荐一 2023-05-08 17:18:14
- 实时焦点:通风管道制作设备,通风管道制作 2023-05-08 17:04:15
- 科学幼小衔接,成都五幼大班萌娃走进小学感悟成长! 2023-05-08 17:09:41
- 中考作文素材:满分句式推荐四_世界速看 2023-05-08 17:06:00
- 每日热闻!中考作文素材:满分句式推荐三 2023-05-08 16:57:54
- 一级建造师视频百度云,一级建造师的视频 今亮点 2023-05-08 17:08:53
- 天天百事通!韶关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招聘170名公告 2023-05-08 17:20:34
- 中考作文素材:满分句式推荐四 2023-05-08 17:14:20
- 武侯计小学子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 2023-05-08 16:59:18
- 高考倒计时,这份小tips请收好!-当前最新 2023-05-08 16:57:09
- 郓城县利民小学:我校开展5.12防灾宣传活动_今日热讯 2023-05-08 17:11:57
- 环球速讯:晋中信息学院赴太原学院调研交流 2023-05-08 17:03:45
- 晋中信息学院赴太原学院调研交流|全球头条 2023-05-08 17:07:12
- 晋中信息学院连续九年中标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高校项目 2023-05-08 17:09:08
- 山西省西部计划项目办一行到晋中信息学院调研宣讲 2023-05-08 17:16:01
- 世界动态:何建新同志任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2023-05-08 16:59:14
- 去美国留学读硕士一年要多少钱 2023-05-08 16:58:16
- 加拿大留学费用一年大概需要多少钱-世界即时 2023-05-08 16:59:15
- 澳大利亚留学费用一年多少-天天最资讯 2023-05-08 17:13:50
- 出国留学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世界时讯 2023-05-08 17:08:59
- 环球百事通!英国留学费用一年多少钱 2023-05-08 17:01:59
- 当前简讯:出国留学有哪些手续 2023-05-08 17:13:44
- 【新要闻】德国留学申请难度大吗 2023-05-08 17:10:05
- 【关注】择机发射! 2023-05-08 16:53:10
- 东北大学在辽宁省“两红两优一先”评选表彰中荣获佳绩 2023-05-08 17:03:26
- 2023年执业药师几月报名 2023-05-08 17:03:39
- 2023年执业药师资格报名时间 每日热点 2023-05-08 17:00:12
- 【速看料】2023年药师啥时候报名考试? 2023-05-08 16:56:00
- 2023河南初会打印准考证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 2023-05-08 17:05:40
- 河南初会打印准考证入口2023|今头条 2023-05-08 16:51:28
- 防震减灾 砥砺前行——方城县梁城希望小学防震演练提自护 2023-05-08 16:47:21
- 郑师附小运动嘉年华,看学子们当“燃”不让 2023-05-08 16:55:38
- 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3 2023-05-08 16:37:02
- 当前焦点!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4 2023-05-08 16:33:29
- 【全球新要闻】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3 2023-05-08 16:32:53
- 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4 2023-05-08 16:35:34
- 青海省2023年高级经济师考试报名5月8日18时截止 全球新视野 2023-05-08 16:46:07
- 世界球精选!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5 2023-05-08 16:40:26
- 江西省2023年高级经济师考试报名5月8日17:00截止|观焦点 2023-05-08 16:53:44
- 世界观焦点:青海省2023年高级经济师考试报名5月8日18时截止 2023-05-08 16:55:10
- 2023年一级造价师《交通运输》阶段测试题5 2023-05-08 16:33:03
- 江西省2023年高级经济师考试报名5月8日17:00截止 2023-05-08 16:43:39